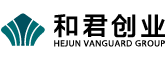達能(néng)糾分(fēn)探源

中(zhōng)國(guó)民(mín)營經濟亟待沖破“原罪瓶頸”
2016年12月29日
中(zhōng)小(xiǎo)股東權益保障也該換換思路了
2016年12月29日達―娃糾紛探源:娃哈哈的改制與達能(néng)的強權—李肅
2007年6月初,我在報上看到達能(néng)揭發檢舉宗慶後的境外離岸公(gōng)司和灰色産(chǎn)權,并在美國(guó)起訴宗慶後妻女,要求高達過百億的賠償,并放出驚世狠話:“讓宗慶後後半生生活在訴訟之中(zhōng)”。這讓我頓悟了達能(néng)娃哈哈之争的本質(zhì)。
最近,中(zhōng)國(guó)經營報開始深入研究娃哈哈的産(chǎn)權問題,涉及到國(guó)企改制及MBO的方方面面。我作(zuò)為(wèi)一個參與中(zhōng)國(guó)企業改革二十年的實踐者,有(yǒu)必要就此發一些感想和議論。
一.娃哈哈的改制真的存在嚴重問題嗎?
娃哈哈的改制源于與達能(néng)合資前四年的1992年。這時,已經創業五年的宗慶後,創設了一家政府持股僅僅20%,經營團隊與員工(gōng)持股達60%的美食城公(gōng)司,并以該公(gōng)司為(wèi)基礎籌劃上市融資。如果美食城公(gōng)司當年上市成功,娃哈哈早已摘掉了今天争論不休的紅帽子。但是,1996年美食城上市受挫,其未能(néng)上市的原因不是企業經營效益太差,而是改制後的職工(gōng)股超标。正是因為(wèi)國(guó)企改制碰到上市難題,才有(yǒu)了百富勤引資達能(néng)的改制空間。
據我們現在看到的資料,娃哈哈1996年 與達能(néng)談判的位勢并不低下,宗慶後堅持自主品牌運營(當時娃哈哈品牌已在全國(guó)打響),堅持中(zhōng)方經營管理(lǐ),堅持維護全體(tǐ)職工(gōng)的一切權益。時至今日,宗慶後還 在為(wèi)當時的談判引以為(wèi)榮。正是因為(wèi)娃哈哈的堅持,達能(néng)把合資範圍定位在與娃哈哈集團局部合作(zuò),五家合資企業之外的多(duō)家子公(gōng)司仍然留在娃哈哈集團。這就是 說,美食城公(gōng)司改制上市失敗後的宗慶後,根本不是經營無奈投靠了達能(néng)公(gōng)司,而是僅僅在部分(fēn)領域與達能(néng)合資合營(當時的理(lǐ)論叫市場換技(jì )術),其他(tā)非合資企業 則由娃哈哈集團獨立經營(與合資企業共同經營娃哈哈的品牌)。這時,宗慶後不可(kě)動搖的既定目标,是繼續推進美食城公(gōng)司起步開始的國(guó)企改制。
2000年到2001年, 杭州上城區(qū)國(guó)資委根據當時國(guó)退民(mín)進的政策,将娃哈哈集團控股權轉讓給宗慶後及企業員工(gōng),集團公(gōng)司的性質(zhì)發生了從國(guó)有(yǒu)到民(mín)營的質(zhì)變。此後,宗慶後與員工(gōng)共創 四家投資公(gōng)司,企業産(chǎn)權完全民(mín)營化。改制以後,娃哈哈與達能(néng)新(xīn)設立的大多(duō)數合資企業,不再由娃哈哈集團投資,而是由宗慶後控股的全新(xīn)主體(tǐ)——廣 盛投資公(gōng)司等四家企業投入。從我國(guó)企業改制的實踐看,這種另設主體(tǐ)的投資方式,是國(guó)企改制後很(hěn)普遍的産(chǎn)權安(ān)排,是國(guó)退民(mín)進的繼續延伸,隻要娃哈哈集團沒有(yǒu) 提出疑異,就是該公(gōng)司認可(kě)的利益安(ān)排和改制延伸。換句話說,如果沒有(yǒu)娃哈哈集團及其股東的認可(kě),這種情況根本不可(kě)能(néng)在長(cháng)達六年中(zhōng)持續發生。至于廣盛投資公(gōng) 司等企業在各地投資的非合資企業,更是四家民(mín)營企業獨立自主的經營行為(wèi),與已經開始國(guó)退民(mín)進的杭州上城區(qū)國(guó)資委沒有(yǒu)任何關系。
涉及到離岸公(gōng)司問題,更是一個帶有(yǒu)中(zhōng)國(guó)國(guó)情的民(mín)營企業常識問題。改革開放之初,合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吸引大批民(mín)營企業(甚至國(guó)有(yǒu)企業)搞概念合資,形成許多(duō)“假洋鬼子”企 業。近年來的海外上市潮,推動一大批民(mín)營企業設立離岸公(gōng)司。所謂離岸公(gōng)司就是在開曼群島等無稅區(qū),為(wèi)各國(guó)企業設立海外運作(zuò)落地點。在不改變原有(yǒu)産(chǎn)權人權益 歸屬的條件下,把企業業績移入離岸地公(gōng)司,以利于在國(guó)外股市上市。這種操作(zuò)模式在國(guó)有(yǒu)企業屬禁止之例,在民(mín)企海外上市中(zhōng)卻比比皆是。在我看來,正是為(wèi)了這 種運作(zuò)模式的需要,宗慶後在後來的合資與投資中(zhōng),必須堅持純民(mín)營公(gōng)司性質(zhì),在沒有(yǒu)國(guó)有(yǒu)資産(chǎn)的條件下操作(zuò)合資合營與海外上市,否則,他(tā)可(kě)真要承擔國(guó)有(yǒu)資産(chǎn)轉 移流失的罪責了。
達 能(néng)想抓住離岸公(gōng)司産(chǎn)權記于宗慶後之女宗馥莉名(míng)下一事,追查産(chǎn)權的合法來源,這可(kě)是對離岸公(gōng)司的嚴重無知。以常理(lǐ)推測,離岸公(gōng)司的這些權益由廣盛投資公(gōng)司等 非國(guó)有(yǒu)企業委托宗馥莉持有(yǒu),是中(zhōng)國(guó)民(mín)營企業最常見的操作(zuò)慣例,似乎沒有(yǒu)什麽玄念可(kě)追。至于其中(zhōng)個别離岸公(gōng)司的法人簽字不實問題,與達娃之争更是毫無直接關 系,不過是離岸公(gōng)司操作(zuò)中(zhōng)的技(jì )術問題,拿(ná)這種問題來小(xiǎo)題大做,隻能(néng)讓人感覺達能(néng)已經黔驢技(jì )窮。
二.國(guó)有(yǒu)企業的MBO真的是大逆不道嗎?
2006年,我在與郎鹹平論戰時,寫了一篇論MBO的文(wén)章,其内容概要如下:
MBO代表了世界發展的趨勢 。郎鹹平從2004年開始批評MBO,他(tā)所依據的基本理(lǐ)論就是常挂在嘴邊的信托責任。在他(tā)看來,美國(guó)1929年的經濟危機,是經理(lǐ)人内部人控制胡作(zuò)非為(wèi)時代的結束,職業經管理(lǐ)人在法律和道德(dé)的雙重約束下回歸“保姆”地位,逐漸安(ān)分(fēn)守己地履行股東約束下的信托責任。
但是,稍有(yǒu)美國(guó)曆史常識的人都會知道,1929年經濟危機之前的美國(guó)企業一直是家族企業的天下,家族式大股東不僅控制經營,而且調動銀行資本參與股票投機。因此,20世紀30年代的一系列法律,一方面是針對銀行的,是把混業經營的銀行強制分(fēn)業管理(lǐ),不許商(shāng)業銀行的存款随意流入股市。另一方面,是針對大股東的,是要求大股東上市拿(ná)到小(xiǎo)股東資本後,不能(néng)随意操縱股市和損害小(xiǎo)股東權益。這裏所說的信托責任絕不是反MBO的理(lǐ)論,而是MBO理(lǐ)論與實踐得以産(chǎn)生的重要基礎。因為(wèi),從20世紀30年開始,家族企業和大股東操縱股市的局面受到強大抑制,為(wèi)日後的經理(lǐ)革命創造了條件。
衆所周知,MBO思想發源于“經理(lǐ)革命”理(lǐ)論,發展于“分(fēn)享經濟”理(lǐ)論,成熟于“知識資本”理(lǐ)論。
MBO的思想發源:
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職業經理(lǐ)人在企業中(zhōng)的作(zuò)用(yòng)與地位發生了質(zhì)變,“經理(lǐ)革命”的理(lǐ)論應運而生。這時的MBO僅限于企業控制權與企業家的激勵獎勵機制,股權領域的全面MBO還隻是個别企業的特例。
MBO 的理(lǐ)論萌芽:
到了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美國(guó)大公(gōng)司全世界擴張,企業的财富驚人集聚,而職業經理(lǐ)人的地位也全面提高,他(tā)們進一步要求利潤分(fēn)享,從而推動“經理(lǐ)革命”理(lǐ)論向“分(fēn)享經濟”理(lǐ)論發展,為(wèi)MBO鋪平了理(lǐ)論之路。從我們目前看到的資料,到20世紀90年代,《财富》排名(míng)前1000家的美國(guó)企業中(zhōng),已有(yǒu)90%的企業推行此計劃,用(yòng)于期權的股票已占到股票總數的10%。
MBO的成熟理(lǐ)論:
1980年,美國(guó)學(xué)者萊特第一次系統研究MBO問題。到了20世紀90年代,MBO理(lǐ)論提升到“知識資本”的層次,人們對三種“知識資本”作(zuò)出了三個時代的理(lǐ)論創新(xīn)與實踐探索。
20世紀80年代的LBO浪潮是在“股東革命”的旗幟下進行的,但給管理(lǐ)性知識資本收購(gòu)企業提供了金融創新(xīn)的經驗,由此刺激管理(lǐ)型人才提高金融素質(zhì),加速推進MBO。
20世紀90年代的信息革命浪潮是以“創業投資”為(wèi)風向标的,它給技(jì )術型知識資本掌控企業和運用(yòng)資本提供了曆史機遇,由此刺激技(jì )術型人才效仿MBO,加速實現企業上市。
21世紀以來的産(chǎn)業基金浪潮是以“全球一體(tǐ)化”為(wèi)動力的,它推動了金融型知識資本運作(zuò)閑置過剩資金,由此刺激金融型人才主導産(chǎn)業整合方向,加速融合三種知識資本在全球聚合與支配無效低價的資金資本。
中(zhōng)國(guó)的國(guó)企改制與MBO
20世紀90年代末和世紀之交,我國(guó)國(guó)有(yǒu)企業在國(guó)退民(mín)進的政策下開始全面改制,其主要方式有(yǒu)三種:
第 一種是因國(guó)有(yǒu)資源能(néng)力不足而産(chǎn)生的自下而上的區(qū)域整體(tǐ)改制。在我國(guó),縣級國(guó)企遠(yuǎn)離市場,缺失人才,很(hěn)少能(néng)有(yǒu)較大的生存空間,國(guó)退民(mín)進基本上以全面退出的方 式賣光。而後,這場改制又(yòu)波及地市級國(guó)企,延伸到省級部分(fēn)嚴重衰退的行業。這種國(guó)有(yǒu)資本的退出,很(hěn)難一家一家企業的個别解決,隻要企業經營者與員工(gōng)積極, 必然以MBO的改制為(wèi)首選方向,并因為(wèi)全地區(qū)全行業改制存在相互比較的壓力機制,多(duō)部門參與的政府機關也必然會産(chǎn)生相互制約的定價機制。
第二種是無法承受産(chǎn)品市場與股票市場雙重壓力的國(guó)有(yǒu)上市公(gōng)司的普遍性重組。20世紀90年代,股票上市是國(guó)有(yǒu)企業的特權,特别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zhōng)期,上市又(yòu)成為(wèi)國(guó)企脫困的重要途徑。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這些公(gōng)司普遍出現經營危機和退市壓力,紛紛進行資産(chǎn)重組,大多(duō)數轉入民(mín)營企業之手,經營無力和資源有(yǒu)限的内部管理(lǐ)層很(hěn)難産(chǎn)生MBO的動力。
第三種是市場化能(néng)力極高的優勢國(guó)企改制。到了世紀之交的2000年前後,我國(guó)的國(guó)有(yǒu)企業還剩下三大部分(fēn),一是壟斷性和資源性的大型國(guó)企,這些企業不可(kě)能(néng)産(chǎn)生MBO的沖動。二是生存空間極小(xiǎo)而社會負擔過大的劣質(zhì)國(guó)企。這些企業沒有(yǒu)一定的改革成本很(hěn)難改制,根本沒有(yǒu)MBO 的機會。三是在競争性行業打拼成功的優勢國(guó)企,有(yǒu)着極大的MBO 動力。
中(zhōng)國(guó)的MBO推進,主要指第三類企業。
研究這類國(guó)企改制,必須搞清以下三個問題。
其一, 優質(zhì)的市場化國(guó)企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國(guó)企,而是一種半紅帽子的混合所有(yǒu)制。
1987年, 我在聯想公(gōng)司做咨詢顧問時,企業上下已經開始讨論産(chǎn)權問題,但當時的曆史條件不可(kě)能(néng)推進企業的改制。十幾年後,聯想的改制又(yòu)提上日程,這時的公(gōng)司規模已達 到當年的幾萬倍,用(yòng)評估轉讓的方法很(hěn)難推進企業改制。最後的解決方案是将聯想公(gōng)司正确歸位為(wèi)半紅帽子的混合所有(yǒu)制企業,35%股權歸為(wèi)國(guó)有(yǒu),35%股權歸于企業經營者,30%股權歸入社會公(gōng)共研究基金,由此推動聯想集團走入了新(xīn)老交替的“二次創業”。
我國(guó)的國(guó)企改革與英國(guó)、蘇東完全不同,它不是在資産(chǎn)平分(fēn)的原點上尋找公(gōng)平方案,而是先在原有(yǒu)産(chǎn)權結構下搞放權讓利的承包制,通過競争性行業長(cháng)時間的激烈競争後,在市場兩極分(fēn)化中(zhōng)開始國(guó)退民(mín)進。其中(zhōng),劣勢企業大多(duō)折價甚至零價改制,由 外資、民(mín)企或内部人接盤。這時,脫穎而出的優勢企業,精(jīng)英人才與全體(tǐ)員工(gōng)雖然創造了巨大的價值并代表着本企業的強勢生産(chǎn)力,卻因為(wèi)國(guó)有(yǒu)企業的攀比機制沒有(yǒu) 得到應有(yǒu)的報酬。如果将這些企業定性為(wèi)完全的國(guó)有(yǒu),具(jù)有(yǒu)明顯的不公(gōng)平性。因此,這些企業的改制本質(zhì)上是一種摘掉半紅帽子的過程,企業産(chǎn)權必須重新(xīn)界定。聯 想集團的改制方案正是解決了這類企業的疑難問題。
其二, 優質(zhì)企業的國(guó)退民(mín)進方向應排他(tā)性選擇代表先進生産(chǎn)力的企業經營層與貢獻較大的企業員工(gōng)。
與 那些衰退了的國(guó)企相比,在競争性行業取勝的優質(zhì)國(guó)企主要靠強大的經營團隊創造了公(gōng)司價值,這些企業長(cháng)期保持國(guó)有(yǒu)機制對長(cháng)遠(yuǎn)競争不利。但是如果把它們等同于 完整意義上的國(guó)企,按郎鹹平的藥方平等競争和公(gōng)平競價,企業的生産(chǎn)力将會遭到根本性的打擊與破壞。我國(guó)這類國(guó)企的公(gōng)開競價經典是完全失敗的健力寶。最為(wèi)戲 劇化的競價場面,是企業經營團隊出價高于外來方,但競價結果卻是代表生産(chǎn)力的管理(lǐ)團隊出局,一個優質(zhì)國(guó)企因此走向衰敗。試想,聯想的改制如果公(gōng)開競價,就 算柳傳志(zhì)花(huā)重金買下公(gōng)司,也會将聯想拖入巨額債務(wù)的深淵。
其三, 市場化的優質(zhì)國(guó)企改制必須對曆史貢獻巨大的企業精(jīng)英階層進行足額折讓,
我國(guó)國(guó)企的MBO不是不可(kě)以開放競争,特别是已經出現衰退迹象的企業,政府有(yǒu)權憑借股東地位提出競标動議。但是,這種競标要以對原有(yǒu)精(jīng)英團隊足額折讓為(wèi)前提。即:在基本條件相同時,依此折讓而優先推進MBO。同理(lǐ)推論,基本條件落差很(hěn)大時,并購(gòu)方進入後要給原有(yǒu)精(jīng)英團隊以足額補償。沒有(yǒu)這一陽光折讓政策,中(zhōng)國(guó)的此類國(guó)企隻能(néng)搞灰色MBO,或者用(yòng)讓利于國(guó)外投資者和民(mín)營企業來變相MBO。一旦上述兩條道路都被堵死,就隻能(néng)铤而走險産(chǎn)生出下一個褚時健了。
3、 曲線(xiàn)MBO是否導緻國(guó)企賤賣外資?
自從2003年财政部叫停大型企業的MBO改制以來,競争性行業中(zhōng)的“國(guó)退民(mín)進”趨勢不會終止,管理(lǐ)層收購(gòu)改制的沖動也不可(kě)能(néng)因此消失,但卻一路轉入“地下”,變成所謂的“隐性MBO”或“曲線(xiàn)MBO”。其中(zhōng),引入外資似乎成了完成此類“隐性”或“曲線(xiàn)”操作(zuò)的一大選擇。
根據公(gōng)開報道,借助外資繞道進行MBO的案例似已有(yǒu)多(duō)例。例如白酒業首例外資并購(gòu)大案,即帝亞吉歐收購(gòu)水井坊股權一事,就有(yǒu)借道外資搞MBO的明顯痕迹。2007年帝亞吉歐出資2.03億元受讓水井坊母公(gōng)司43%的股權,等于間接持股水井坊達17%即8305萬股,簡單計算每股價格不到2.50元,而水井坊的二級市場價卻一直在13元以上,僅此一項,外方的收購(gòu)獲利就達10億元,這還不包括全興酒精(jīng)旗下的其他(tā)企業。據分(fēn)析原因也很(hěn)簡單:水井坊高管層做MBO有(yǒu)1.4億的資金缺口,而引進外資卻有(yǒu)效地使他(tā)們能(néng)夠套現巨額現金。又(yòu)如高盛并購(gòu)雙彙集團,一個有(yǒu)60多(duō)家子公(gōng)司、銷售額 200 億元以上、總資産(chǎn) 50 多(duō)億元、中(zhōng)國(guó)最大的肉類食品加工(gōng)集團,僅僅20億元就賣出,一直被人懷疑猜測這可(kě)能(néng)是一出曲線(xiàn) MBO ,意在借力海外過橋資金實現管理(lǐ)層持股。引發過巨大争議的徐工(gōng)出售給美國(guó)凱雷一案,同樣有(yǒu)類似問題,雖然徐工(gōng)出售因一直未被批準而擱置下來。
如果對中(zhōng)國(guó)2000年以來的外資收購(gòu)做一個較全面的調查,誰又(yòu)知道還有(yǒu)多(duō)少含有(yǒu)繞道MBO成分(fēn)的案例發生?今天争執厮打成這個樣子的達能(néng)—娃哈哈合資案例,僅僅一年多(duō)前還被人當作(zuò)是“跨國(guó)婚配”的“模範夫妻”,但其中(zhōng)卻暗含了這麽多(duō)“隐性MBO”所必然帶來的内部矛盾伏筆(bǐ),說是處處暗雷亦不為(wèi)過。這就是說:中(zhōng)國(guó)人自己名(míng)正言順的“陽光MBO”該做卻不能(néng)做,于是就借助五花(huā)八門的變通方式來做,特别是借助具(jù)有(yǒu)突出的“涉外優惠”的外資引進來做。這無論如何讓我想起一句也許不恰當、但卻頗為(wèi)貼切的老話:“甯贈友邦,不與家奴”!無數的事實與案例都表明,進行相對透明的、受相應法規管理(lǐ)的正當MBO,無疑是發展企業、保障生産(chǎn)力發展延續性和長(cháng)久性的有(yǒu)效辦(bàn)法,其中(zhōng)最大的好處不僅是避免損毀生産(chǎn)力和社會财富,而且有(yǒu)助于培育發展中(zhōng)國(guó)人自己的企業家人才,而“知識型管理(lǐ)人力資本”又(yòu)是國(guó)家間競争的根本要素之一,但卻不能(néng)搞也不讓搞,被社會輿論說成是洪水猛獸與大逆不道。那麽問題絕不消失,而是曲折變态。其中(zhōng)最不好的後果,恰恰就是達能(néng)—娃哈哈的糾紛争執案例。
綜上所述,中(zhōng)國(guó)國(guó)企的MBO是一個極為(wèi)複雜的改革難題。郎鹹平不僅不了解這一難題的全部曆史,而且不了解關鍵難點的産(chǎn)生背景和問題實質(zhì),無知又(yòu)無畏地進行了一場誤導國(guó)企改革的反MBO運動,并對中(zhōng)國(guó)的改革與發展産(chǎn)生了極其惡劣的不良影響。今天,達能(néng)公(gōng)司為(wèi)了廉價收購(gòu)娃哈哈的一己私利,突然又(yòu)成了反MBO的鬥士,讓我不能(néng)不在緻達能(néng)公(gōng)司的公(gōng)開信中(zhōng)批評達能(néng): “達能(néng)公(gōng)司作(zuò)為(wèi)國(guó)企改制中(zhōng)的“繞道M BO”的受益者,拿(ná)到了顯失公(gōng)平的娃哈哈商(shāng)标權;但到了雙方利益發展失衡、并産(chǎn)生沖突後,達能(néng)又(yòu)不擇手段地”“用(yòng)離岸公(gōng)司、美國(guó)身份和繞道M BO等方面的灰色地帶揭對方的醜,以達到顯失公(gōng)平的進一步收購(gòu)兼并目的。這種做法,在商(shāng)業道德(dé)上有(yǒu)失跨國(guó)公(gōng)司的商(shāng)業風範。”
三.隐性MBO是達娃之争産(chǎn)生的根源嗎?
2007年6月,我在緻達能(néng)公(gōng)司的公(gōng)開信中(zhōng)指出:在我國(guó),"為(wèi)什麽徐工(gōng)的問題沸沸揚揚?雙彙合資疑雲滿天?娃哈哈之争各執一詞?究其根源,還是中(zhōng)國(guó)反MBO浪 潮與社會仇富心态壓力下,導緻上述企業往往不得不借合資進行産(chǎn)權改制,在簽訂合資合同中(zhōng)往往因此而産(chǎn)生顯失公(gōng)平的現象。外國(guó)資本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利用(yòng)了 企業特殊的産(chǎn)權改革困境,而取得了有(yǒu)違商(shāng)業原則的不公(gōng)平合同"。國(guó)浩律師所的李淳律師在搜狐網與我辯論,說我把達娃之争的背景複雜化。但是,從後來達能(néng)公(gōng) 司的一系列舉動去看,這一複雜背景根本不可(kě)回避。
在我看來,中(zhōng)國(guó)半紅帽子的優勢國(guó)企如果能(néng)在完成MBO改 制後,再來進行合資合營談判,根本不可(kě)能(néng)出現徐工(gōng)困局與達娃之争,因為(wèi),徐工(gōng)困局産(chǎn)生于經營團隊低估國(guó)有(yǒu)資産(chǎn),希望借助凱雷進入實現經營者持股,由此引發 出向文(wén)波的種種質(zhì)疑。同樣,娃哈哈在美食城改制上市失敗後,并不是走投無路賣身投靠,而是希望實現外資控股和無形資産(chǎn)轉移,并在此環境下平穩推進MBO。因此,娃哈哈與達能(néng)從合作(zuò)之初就已經定下了南轅北轍的戰略目标。宗慶後要在合資的同時繼續推進國(guó)企改制,并用(yòng)市場換回技(jì )術後發展壯大娃哈哈集團;達能(néng)則想在合資後繼續全面并購(gòu),不惜同業競争也要通吃中(zhōng)國(guó)的其它飲料企業。
綜上所述,娃哈哈的隐性MBO,是誘發達能(néng)公(gōng)司霸道強權的重要原因。如果當年不出現反MBO潮流,如果宗慶後早已買斷娃哈哈集團中(zhōng)的所有(yǒu)政府産(chǎn)權,今天的這場改制是非之争不可(kě)能(néng)爆發。達能(néng)公(gōng)司也不可(kě)能(néng)産(chǎn)生出可(kě)以置宗慶後于死地的錯覺,更不可(kě)能(néng)以如此極端的方式來利用(yòng)中(zhōng)國(guó)的反MBO情緒和社會仇富心态,借助中(zhōng)國(guó)的反改革勢力。我從來是一個國(guó)企改制的倡導者,并在MBO問題上堅決反對郎鹹平的國(guó)企改革失敗論。為(wèi)此,我在緻達能(néng)公(gōng)司的公(gōng)開信中(zhōng)明确指出:"作(zuò)為(wèi)中(zhōng)國(guó)M BO的積極主張者,我強烈反對達能(néng)公(gōng)司近期的行為(wèi),并認為(wèi)這場商(shāng)業利益之争,正在被達能(néng)轉化為(wèi)一場阻礙國(guó)企産(chǎn)權改革的體(tǐ)制之争。因此,能(néng)否制止達能(néng)公(gōng)司取得顯失公(gōng)平的利益和推進娃哈哈的全面改制,已經成為(wèi)中(zhōng)國(guó)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