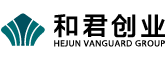懲治“民(mín)企原罪”是對和諧社會與有(yǒu)效反腐的嚴重威脅

和君創業對咨詢的理(lǐ)解
2016年12月29日
中(zhōng)國(guó)民(mín)營經濟亟待沖破“原罪瓶頸”
2016年12月29日作(zuò)者:李肅
最近,全國(guó)工(gōng)商(shāng)聯副主席胡德(dé)平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出,“清算民(mín)企的第一桶金,是對我國(guó)改革的根本否定。”講話一出,語驚四座,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贊同支持之聲有(yǒu)之,強烈異議之人四起,其争論的焦點集中(zhōng)于怎樣看待民(mín)企第一桶金的“原罪現象”。贊同者認為(wèi)清算民(mín)企第一桶金,會引來改革開放先行者與成功者的極大恐慌,嚴重破壞民(mín)企繼續深化改革的前進動力。反對者認為(wèi)民(mín)企第一桶金充滿權錢交易的黑洞,是造成社會不公(gōng)的根源,不清算原罪何以維護社會公(gōng)正與法律尊嚴。在這裏,改革與“反腐”居然變成了“魚與熊掌不可(kě)兼得”的對立之物(wù)。我認為(wèi),出現這一“悖論”和思想混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從來沒有(yǒu)人做過“原罪”與“犯罪”的本質(zhì)區(qū)分(fēn);不澄清這一點,思想的混亂會愈演愈烈,深化體(tǐ)制改革與建設和諧社會都将無從談起。為(wèi)此,我想以咨詢服務(wù)于中(zhōng)國(guó)企業二十年的經驗和感受,對“原罪現象”發表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正确區(qū)分(fēn)“原罪”與“犯罪”是理(lǐ)解民(mín)企第一桶金問題的關鍵
我認為(wèi),民(mín)企“原罪”是一種具(jù)有(yǒu)曆史進步性和曆史必然性的經濟違規現象,随着改革發展的三個階段而有(yǒu)三種基本形态。
1. 八十年代“摸着石頭過河”探索中(zhōng)的起步改革期,民(mín)營企業的違紀違規較多(duō)的集中(zhōng)于對舊體(tǐ)制的“邊緣突破”,是一種“改革性的探索原罪”,是改革界線(xiàn)不清産(chǎn)生的無知之罪。
當時,我國(guó)的經濟體(tǐ)制建立在大一統的公(gōng)有(yǒu)制基礎上,全盤包辦(bàn)式的計劃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 民(mín)營企業的每一步發展都是以突破法紀為(wèi)前提條件,農村承包責任制在偷偷摸摸的違法中(zhōng)探索,溫州的長(cháng)途販運者被當成投機倒把槍斃。正如著名(míng)經濟學(xué)家吳敬琏所說:中(zhōng)國(guó)的經濟改革表面上看是“漸進式改革”,但實際的核心卻是“體(tǐ)制外突破”;在現實經濟生活中(zhōng)大量的“難題”與“破題”,往往蘊藏在明裏暗裏針對舊體(tǐ)制弊端的挑戰違反與突破消解之中(zhōng),大量“體(tǐ)制外”的民(mín)營創業者們在一系列形無實有(yǒu)的“法規邊界線(xiàn)”上出出進進、“摸着石頭過河”。當體(tǐ)制内的惰性使改革很(hěn)難有(yǒu)所進展之時,“體(tǐ)制外經濟”不斷打破舊體(tǐ)制常規的束縛就成為(wèi)必然現象。制度不合理(lǐ)的龐大存在,以及民(mín)營經濟實際上的“非法狀态”和“非法行為(wèi)”,必将導緻一系列不可(kě)避免的原罪現象,這就是所謂對舊體(tǐ)制“邊緣突破”的改革性探索原罪。從金融改革的趨勢上看孫大午的非法集資,其本質(zhì)不過是一種特殊的私募融資,此類行為(wèi)屬典型的“改革性探索原罪”。
總之,“改革性探索原罪”基本上是針對舊體(tǐ)制而言的概念,是一個與權力包辦(bàn)式經濟和政府包辦(bàn)型社會相對立的概念,對這個原有(yǒu)的社會–經濟體(tǐ)制來說,鄧小(xiǎo)平提倡的“摸着石頭過河”本身就是典型的“原罪号召”,并構成“改革性探索原罪”産(chǎn)生的“第一推動力”。因此,凡是對舊體(tǐ)制沖擊和打破的民(mín)企操作(zuò),隻要代表未來改革趨勢的行為(wèi),都可(kě)視為(wèi)“原罪”而非犯罪。時至今日,改革大業并未完成,大量舊體(tǐ)制下的法律有(yǒu)待改革,由于民(mín)營企業受到的行政制約最小(xiǎo),其“邊緣突破”的能(néng)力最強。因此,面對這種“邊緣突破”舊體(tǐ)制的“改革性原罪”,必須劃清現行法律與改革趨勢的界線(xiàn),隻要改革仍在進行,就應該更多(duō)地關注後者,用(yòng)後者的實踐推動前者的變革。
2、九十年代“三個代表理(lǐ)論”形成中(zhōng)的深化改革期,民(mín)營企業的違規違法更多(duō)地表現為(wèi)配合地方政府推進地方經濟發展而進行的“跟随違法”,是一種“發展性的被動原罪”,是政府官員主導下發生的曆史之罪。
進入九十年代之後,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動力受三種因素刺激:一是南巡講話的改革開放推動力;二是經濟緊縮後的就業壓迫力;三是稅收體(tǐ)制改革後的地方政府的職能(néng)轉變力,三力合一導緻一場波及全國(guó)的“地方經濟發展大競賽”。這時的民(mín)營企業已逐漸成為(wèi)地方經濟的主導力量,許多(duō)政府為(wèi)發展地方經濟推出各種追求超常發展的“土政策創新(xīn)”,其落實對象多(duō)是機制更活的民(mín)企,各種形式的“政策贖買”,“資源交易”,大多(duō)表現為(wèi)經濟人與政府人間五花(huā)八門的合謀共串,甚至幹脆是政府授意所為(wèi),導緻了“灰色交易地帶”的蔓延。
我國(guó)的發展與改革在政府擁有(yǒu)大部分(fēn)資源與絕對性權威的起點上展開,民(mín)營企業作(zuò)為(wèi)幼稚的生産(chǎn)力,隻有(yǒu)依賴于政府的支持,按政府官員的意志(zhì)行事。這就是所謂的“政府強權産(chǎn)生民(mín)企原罪”。因此,分(fēn)析“原罪土壤”應遠(yuǎn)重于“清算原罪”,不能(néng)隻問結果不問因由,特定的曆史轉型期,特定的曆史改革與轉型任務(wù),特定的“原罪土壤環境”,決定了環境中(zhōng)民(mín)營企業快速發展的行為(wèi)方式。所謂“鐵本事件”,就是典型的政府違規而民(mín)企受難。
我 國(guó)民(mín)營企業迅猛發展,與地方政府對民(mín)營企業的全力支持緊密相聯,與官商(shāng)密切配合不可(kě)分(fēn)割。在日本、在南韓,這種官商(shāng)關系與銀企關系,是在陽光下公(gōng)開進行 的,但在我國(guó)的九十年代,民(mín)營企業的分(fēn)化沒有(yǒu)完成,發展地方經濟的機會稍縱既逝,重大項目的政府資源配置難以形成透明規則,在此背景下出現一些違法違規的 混亂在所難免。但是,不管是惡意犯罪還是善意違規,有(yǒu)兩點必須澄清:
第一,中(zhōng)國(guó)以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向市場主導的資源配置轉型中(zhōng),腐敗的最大根源,在于權力包辦(bàn)經濟,由此産(chǎn)生社會經濟實體(tǐ)對權力的“配合”與“供養”。因此,權錢交易的責任主導方面在于強勢的政府,而不能(néng)一味追究弱勢的民(mín)營企業家。既便是在明顯的索賄受賄事件中(zhōng),證據采信的重點也應更多(duō)地相信民(mín)企“被動違法”的一面,側重懲治索賄受賄的不法官員。
第二,我們也必須分(fēn)清政府官員惡意犯罪與善意違規的界線(xiàn),在和諧社會的反腐敗工(gōng)作(zuò)中(zhōng),要正确地把握方向,不能(néng)用(yòng)個别官員的腐化全盤否定整個政府發展經濟的動機,更不能(néng)不分(fēn)原罪産(chǎn)生的主動被動背景,把民(mín)企的第一桶金當官商(shāng)勾結的主因來全面清算。
目前看,原罪之争的焦點是民(mín)企第一桶金中(zhōng)的權錢交易,主張清算原罪者們最大的錯誤,是把民(mín)企當作(zuò)腐敗産(chǎn)生的罪魁而不是腐敗現象的受害者。我們認為(wèi),“反腐”不是“反富”,反腐倡廉與殺富濟貧有(yǒu)天壤之别,民(mín)營企業是反腐敗的同盟軍。如果把民(mín)營企業當反腐大敵,将矛頭直指跟随違法的被動一方,不僅會錯誤打擊無辜的民(mín)企生産(chǎn)力,而且會把“反腐倡廉”引到“殺富濟貧”的邪路上去。
3、二十一世紀“科(kē)學(xué)發展觀’推進中(zhōng)的和諧改革期,民(mín)營企業的違法犯罪主要體(tǐ)現為(wèi)法不責衆的“行規慣性”還在延續,由此産(chǎn)生出“普遍性的道德(dé)原罪” ,形成民(mín)企經濟發展“原功”支撐下的可(kě)同情之罪。
“行規慣性”的原罪是指在特定條件下,企業普遍性的違法犯罪。其中(zhōng),有(yǒu)些是經濟緊縮時企業被迫采用(yòng)的應變措施,有(yǒu)些是政府土政策支持的普遍違法,有(yǒu)些是行内競争需要互相攀比形成的違法犯罪。這些原罪都有(yǒu)一個共性,在産(chǎn)生之時有(yǒu)着明顯的行業道德(dé)支持,是一種“法不責衆”的“行規慣性”,是民(mín)營企業“普遍性的道德(dé)原罪”。這類犯罪在八十年代價格雙軌制下較多(duō)産(chǎn)生于官倒尋租牟利;九十年代初集中(zhōng)于土地交易的暗箱操作(zuò);九十年代中(zhōng)表現為(wèi)大股東占用(yòng)資金盛行;九十年代末則是自下而上的運動式國(guó)企改制,等等。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 仍有(yǒu)大量“行規慣性”的“普遍性的道德(dé)原罪”在民(mín)企中(zhōng)流行,德(dé)隆唐萬新(xīn)的罪名(míng)均屬此類。
民(mín)企這一類的“違法”甚至“犯罪”,無人追究并形成“行業慣性”,與民(mín)企“市場經濟原功”直接相關。我國(guó)民(mín)營企業從個體(tǐ)創業發展到占全國(guó)GDP50%以上,并在競争性行業占據主導地位,在制造業領域建成舉世公(gōng)認的“世界工(gōng)廠”,為(wèi)中(zhōng)國(guó)經濟起飛立下了不可(kě)磨滅的“原功”。各種形式的政府宏觀調控往往會直接影響某些個地區(qū)或某些行業的發展,此時的為(wèi)發揮民(mín)企市場發展力的“原功能(néng)量”,必然出現“見了紅燈繞着走”等等違規或變相違規的現象,被為(wèi)其他(tā)企業普遍效法,成為(wèi)支持違法犯罪的道德(dé)基礎,形成法不責衆的“行規慣性”,産(chǎn)生出“普遍性的道德(dé)原罪” 。從這一意義上區(qū)分(fēn)原罪與犯罪,主要兩個重要标志(zhì),一是看其經濟“原功”的性質(zhì)是為(wèi)一己私利還是為(wèi)富一方經濟;二是看其道德(dé)支撐的範圍有(yǒu)多(duō)大的普遍性。
總 之,民(mín)企原罪是一種複雜的曆史現象,需要有(yǒu)極高理(lǐ)論素質(zhì)和政治智慧,極強的政策水平和司法技(jì )巧加以解決。以科(kē)龍案為(wèi)例,顧雛軍是集上述三種原罪于一身者。 從其行為(wèi)和指導思想上看,顧對舊體(tǐ)制的沖擊是無處不在的,例如在企業注冊登記方面,四處挑戰工(gōng)商(shāng)企業登記和對外投資的舊法規,構成了“邊緣突破”的改革性探索原罪;在重組各地衰敗企業時,充分(fēn)利用(yòng)格林科(kē)爾的靈活機制,受到地方政府的全力推動與支持,形成了“跟随違法”的“發展性被動原罪”;而其最重的挪用(yòng)上市公(gōng)司資金的犯罪,是典型的“行規慣性”犯罪,具(jù)有(yǒu)“普遍性道德(dé)原罪”的全部屬性。如果按此準則全面清算“第一桶金”并嚴厲懲治“民(mín)企原罪”,必将在新(xīn)的曆史條件下制造大量新(xīn)的冤假錯案。
二、解決“民(mín)企原罪”是建設和諧社會與有(yǒu)效反腐的重要基礎
最近,我們在為(wèi)國(guó)内很(hěn)多(duō)民(mín)營企業,特别是潛力大、根基好的大中(zhōng)型民(mín)企的咨詢服務(wù)中(zhōng)深切地感到,民(mín)營企業領導人對我國(guó)業已進入超日趕美的經濟形勢普遍缺少激情,對企業面臨的很(hěn)好的擴張機遇有(yǒu)明顯的退縮心态。究其原因,是因為(wèi)他(tā)們面對目前社會上迅速蔓延的仇富心态,尤其是頗為(wèi)泛濫的追究“民(mín)企原罪”的思潮,以及對一個又(yòu)一個知名(míng)企業家的先後落馬入獄也感人人自危,很(hěn)多(duō)人幾乎到了惶惶不可(kě)終日的地步!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zhōng)央統戰部胡德(dé)平副部長(cháng)提出“追究民(mín)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績”的判斷,引起了全社會的強烈反響,我國(guó)第三次改革論争已漸露端倪。如果說80年代第一次改革論争集中(zhōng)于要不要搞改革的左派右派之争,90年代的第二次改革論争聚焦于限不限制改革的姓社姓資之争,21世紀第三次改革論争已轉到停不停止改革的“公(gōng)平效率”之争上來。民(mín)企第一桶金的原罪問題牽涉到改革曆史的評價問題和“怎樣繼深化續改革”,成為(wèi)第三次改革論争的重要聚焦點,關系到和諧社會建設的成敗興衰。
公(gōng)平與效率是現代社會永恒性話題。黨的十六屆六中(zhōng)全會在建設和諧社會方面十分(fēn)重視公(gōng)平問題,而“國(guó)務(wù)院關于民(mín)營企業發展的36條”,着眼于提高民(mín)企效率,其目标,都是建設公(gōng)平與效率統一的和諧社會。但是近一度來,恰恰有(yǒu)一股“左”的思潮再度擡頭,且在社會上滋生蔓延。不加區(qū)分(fēn)地“清算民(mín)企原罪”,正是這種思想風潮的集中(zhōng)反映,它不僅給20多(duō)年來做為(wèi)改革先行者的民(mín)營企業家背上沉重的“原罪包袱”,也對和諧社會的建設産(chǎn)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為(wèi)此,我們認為(wèi)應該從以下四個方面探讨“民(mín)企原罪”的解決之道。
從曆史層面上講,上世紀新(xīn)中(zhōng)國(guó)成立初期,中(zhōng)國(guó)的民(mín)族資本已有(yǒu)超過半個世紀的發展曆史,大量的“原罪磨合”過程多(duō)已完成,行業誠信水平、市場規則的建立都達到一定水準,如果按照當時劉少奇等領導人的思路發展下來,中(zhōng)國(guó)經濟早15年到20年進入起飛階段,我們也沒必要再經曆痛苦的“原罪磨合期”。如果我們重複曆史錯誤,借懲治原罪再次打壓民(mín)營經濟,不僅會廣泛引起社會仇富情緒,中(zhōng)國(guó)也将會重新(xīn)經曆一系列發展之苦,這無疑是對社會和諧發展的嚴重威脅。
從思想認識層面講,在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zhōng),要警惕“左”的思想擡頭,更要防止“階級鬥争”和“繼續革命”的社會思潮重現,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時間中(zhōng),民(mín)營企業的原罪懲治之風刺激了社會仇富心态的蔓延,嚴重挫傷着民(mín)營企業和民(mín)營企業家的發展積極性,并明顯阻礙了社會生産(chǎn)力的發展,并嚴重破壞着和諧社會的建設。
從 國(guó)家政策層面講,我國(guó)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與和諧為(wèi)本的社會政策,都需要民(mín)營企業大發展作(zuò)為(wèi)物(wù)質(zhì)保證。因此,怎樣運用(yòng)強有(yǒu)力的經濟政策與産(chǎn)業政策扶植民(mín)企發 展,怎樣在科(kē)學(xué)發展觀指導下深化改革,給民(mín)營企業的未來發展創造更好環境,已成為(wèi)提高民(mín)企自主創新(xīn)力和國(guó)際競争力的重要前提。當前,在和諧社會建設的關鍵 時期,我國(guó)民(mín)營健康發展的當務(wù)之急,是正确處理(lǐ)好民(mín)營企業的原罪問題,讓民(mín)營企業家能(néng)有(yǒu)最基本的生存安(ān)全感。為(wèi)此,我們應該學(xué)習南非解決種族沖突原罪的經 驗,按時間界限或規定條件解脫民(mín)企原罪。
從立法執法層面講,首先要正确區(qū)分(fēn)“原罪”與犯罪,認定為(wèi)犯罪的,就要依法懲處;對于原罪問題,要根據三種原罪制定不同的執法原則。首先,要鼓勵和支持并非真正犯罪的“改革性探索原罪”,通過法院法官的判例立法,解決改革實踐與立法滞後的矛盾。其次,要曆史地看待官商(shāng)關系産(chǎn)生的“發展性被動原罪”,在反腐敗工(gōng)作(zuò)中(zhōng)嚴格掌握政策,更多(duō)地鼓勵企業家揭露腐敗,更好地保護民(mín)營企業的先進生産(chǎn)力。同時,要赦免在特定曆史條件下民(mín)企經濟“原功”支撐下産(chǎn)生的“普遍性道德(dé)原罪”,要在全國(guó)人大建立聽證會制度,解決原罪劃界問題。全世界大部分(fēn)市場經濟發達國(guó)家都對經濟生活中(zhōng)類似現象有(yǒu)道德(dé)免責通道,作(zuò)為(wèi)轉型國(guó)家,我們的情況複雜得多(duō),更要重視建立健全行政首長(cháng)的赦免權行使制度。
綜上所述,清算民(mín)企“原罪”,意味着對改革實踐本身的清算,意味着無視于整個改革曆程,意味着不認可(kě)改革必有(yǒu)的曲折性,同時也意味着最具(jù)腐敗根源性的權力化經濟借“國(guó)進民(mín)退”之風重新(xīn)複辟。因此,清算“民(mín)企原罪”就是對曆史的犯罪,我國(guó)立法機構有(yǒu)責任盡快制止這種社會性犯罪,以保障和諧社會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