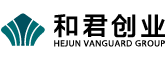中(zhōng)國(guó)民(mín)營經濟亟待沖破“原罪瓶頸”

懲治“民(mín)企原罪”是對和諧社會與有(yǒu)效反腐的嚴重威脅
2016年12月29日
達能(néng)糾分(fēn)探源
2016年12月29日作(zuò)者:李肅
在“民(mín)企富豪”接連被抓并引發社會仇富思潮異常湧動的背後,中(zhōng)國(guó)民(mín)營企業創業者所遭受的離奇冤案,是一般民(mín)衆所遠(yuǎn)不了解的。江西新(xīn)大地公(gōng)司的董事長(cháng)塗景新(xīn)因“貪污”和“挪用(yòng)”自己所創的公(gōng)司财富而被判死緩,3年後又(yòu)被戲劇性地改判無罪,就是非常離奇而典型的一例。他(tā)在80年代末所一手創建的新(xīn)大地公(gōng)司,以華東地區(qū)最紅火、最具(jù)影響力的南昌IT市場為(wèi)核心,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僅僅借用(yòng)國(guó)營名(míng)義的“紅帽子公(gōng)司”,按照國(guó)家法律所認可(kě)的“誰出資、誰擁有(yǒu)”原則,完全應該屬他(tā)自家所有(yǒu)。但在這一離奇冤案的終審判決上,這家年盈利上千萬元的企業卻最終判給了既無出資、又(yòu)無貢獻的“挂靠單位”——海南機械設備進出口公(gōng)司(海機設)。塗景新(xīn)在二審中(zhōng)能(néng)夠逃得性命、全身而退已屬異數,當然不敢再生枝節去搶回自家産(chǎn)權了。紅帽子企業“摘帽”,這種在今天本來已經很(hěn)常見、很(hěn)普通的改制問題,也居然鬧到了判決死刑的地步,足見中(zhōng)國(guó)社會懲治民(mín)企原罪之風,已刮到了多(duō)麽嚴重的程度。
僅僅從塗景新(xīn)一個案子,就足以看出,作(zuò)為(wèi)中(zhōng)國(guó)經濟中(zhōng)最有(yǒu)活力、最有(yǒu)未來代表性的民(mín)營經濟,已經的的确确處在一個前所未有(yǒu)的發展危機之中(zhōng)了。更何況借懲治民(mín)企原罪,以搶奪民(mín)企财富成果的案例幾乎到處都有(yǒu),遠(yuǎn)遠(yuǎn)不止塗景新(xīn)案這一例所能(néng)涵蓋。
一、終審判決隻是案件開端,保護民(mín)企産(chǎn)權成為(wèi)突出焦點
首先我認為(wèi),終審無罪判決不是該案的結束,而是該案真正開始的起點。原因很(hěn)簡單:該案的核心與關鍵,根本就不是也不應是刑事犯罪意義上的“是否侵吞了國(guó)有(yǒu)資産(chǎn)”,而是能(néng)否有(yǒu)效保障民(mín)企産(chǎn)權或民(mín)營企業家收益權等正當權益。
從 案件的法律角度而言,由于一上來就是以刑事司法方式高調介入,把一個本屬民(mín)事糾紛的問題直接上升到了刑法高度,所以事實上産(chǎn)權争議已根本無機會進入訴訟。 而之所以能(néng)夠從死緩改為(wèi)無罪,完成如此巨大的判決跨度,實際上是以訴訟技(jì )術處理(lǐ)的巧妙變通打了兩張牌而達到的。一是據以判罪的2500多(duō)萬元收入是否屬于公(gōng)司說不清,來源不明,缺乏證據;二是這收入在長(cháng)達六七年的過程中(zhōng)用(yòng)到哪了也說不清,由于塗景新(xīn)把公(gōng)司看做是個人的,更多(duō)的還是用(yòng)于公(gōng)司業務(wù),難以構成貪污。一進一出兩頭難定,這樣,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最終判決無罪。那麽應該說這是訴訟技(jì )巧上的“勝利”,而不是法律和司法進步的勝利。這樣一來隻是把原來莫須有(yǒu)的罪名(míng)取消了,并沒有(yǒu)把應該解決的問題真正解決。
真正應該解決的,恰恰就是民(mín)營企業真實準确的産(chǎn)權所有(yǒu)關系。既然是“誰出資、誰擁有(yǒu)”,既然新(xīn)大地公(gōng)司由塗本人出資建立,既然海機設僅是出具(jù)了空頭證明,沒有(yǒu)實際出資,那麽公(gōng)司産(chǎn)權本來應該是塗景新(xīn)的。3年艱苦的維權“終成正果”,但隻解決了刑事冤案的問題,并沒有(yǒu)解決保護民(mín)企産(chǎn)權、維護民(mín)營經濟正當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因此我認為(wèi),刑事訴訟的結束應該是繼續民(mín)事訴訟官司的開端;無罪判決也不是維權行為(wèi)的結束或勝利,而是真正維權行動開始的前提。
應該怎麽做?至少可(kě)有(yǒu)兩個途徑,重啓訴訟。
一是直接打工(gōng)商(shāng)行政訴訟,将推翻了原有(yǒu)改制變更的年的工(gōng)商(shāng)裁決再次推翻。這條路難度不小(xiǎo),但在法律上站得住。一則300餘萬公(gōng)司初始投資均來自塗景新(xīn),二則以國(guó)有(yǒu)身分(fēn)獲得的一千萬元銀行借貸不僅有(yǒu)塗本人房産(chǎn)為(wèi)抵押,而且事後在改制脫鈎時還做了債務(wù)轉移,改制應有(yǒu)的程序也基本到位,産(chǎn)權更有(yǒu)理(lǐ)由定性為(wèi)民(mín)營。至于說“有(yǒu)難度”,是因為(wèi)塗的當案辯護律師稱,此案背景複雜,如果我方提起産(chǎn)權訴訟,海南檢察院很(hěn)可(kě)能(néng)會挑該案二審審理(lǐ)方式上的漏洞,對無罪判決重提抗訴,使事情更加複雜。因此他(tā)反對繼續維權的主張。
二是打“國(guó)企承包”訴訟。假定當案律師的擔憂成立,直接打産(chǎn)權官司有(yǒu)所不便,那麽即使按照承包契約,正當的承包收益也應受到法律保護,塗景新(xīn)的合法承包所得一千多(duō)萬也應歸還,而不應被非法剝奪。從各個關鍵事實看,打承包訴訟在法理(lǐ)上同樣完全站得住腳,
既然該案(以及其他(tā)類似的衆多(duō)民(mín)企案件)的核心焦點在于對民(mín)營産(chǎn)權的保護,那麽對此的任何退讓和放棄都将會開啓司法史與經濟史上的惡案先例,使得其他(tā)所有(yǒu)想借抓民(mín)企原罪而搶奪産(chǎn)權利益的人感覺易于得逞,使本來就處在危機中(zhōng)的民(mín)營經濟的合法權益變得更加岌岌可(kě)危。
二、“懲治原罪”是塗景新(xīn)案及其他(tā)民(mín)企案件的要害所在
詳 細的了解表明,通過懲治民(mín)企原罪,肆無忌憚地侵害民(mín)企産(chǎn)權,搶奪民(mín)企财富成果,是此類案件的根結要害所在。最近我對科(kē)龍顧雛軍案、天發龔家龔案、鐵本戴國(guó) 芳案等一批民(mín)營企業家落馬被抓案件做了詳細了解和分(fēn)析,充分(fēn)印證了這一判斷。象顧雛軍案的不少罪名(míng)都是非常牽強甚至很(hěn)難成立的,而且不許他(tā)申訴,不許他(tā)揭 發有(yǒu)關官員,不許他(tā)公(gōng)開相關重要證據。其背後的核心就是地方政府要搶他(tā)的産(chǎn)權。龔家龍案更為(wèi)典型,先後3年多(duō)時間裏,政府四次正式下達紅頭文(wén)件确認他(tā)的民(mín)營産(chǎn)權,又(yòu)四次無理(lǐ)推翻,而且多(duō)次以抓捕治罪相威脅,迫其交出企業産(chǎn)權,還把搶來的企業(天頤科(kē)技(jì ))交給政府官員親近的個體(tǐ)戶經營,經營失敗後又(yòu)居然用(yòng)老幹部基金的5000萬元為(wèi)其墊資脫身!借“懲治原罪”以 搶奪利益成果的真實意圖,簡直到了毫不掩飾和明目張膽的地步。鐵本戴國(guó)芳案更是如此。本來繞過中(zhōng)央調控、上大鋼鐵項目就是當地政府一手操辦(bàn)的,嫁接利用(yòng)戴 國(guó)芳的小(xiǎo)鋼鐵企業也是地方政府強意所為(wèi),中(zhōng)央的宏觀調控針對的是地方政府,罪責和損失無論如何不應由被強迫參與的戴來承擔。但實際上,不僅把完全無罪的戴 抓捕至今(已逾3年),而且把他(tā)的鋼廠随意派交給一個體(tǐ)戶,每年近億的利潤僅上報800萬,利益大頭流到哪裏無人能(néng)知,形成了極大的利益黑洞。
綜上各案可(kě)以清楚看出,這裏的矛盾本質(zhì)根本不是什麽“富豪與民(mín)衆”、“富人與窮人”間的對立,而是地方政府或某些權勢者,在利用(yòng)司法及行政公(gōng)權搶奪民(mín)間私利;名(míng)借反腐,實則反富,以達其暗中(zhōng)私利。被搶奪的産(chǎn)權成果也決不會“均貧富”到百姓頭上,要麽流入權勢黑洞,要麽幹脆把本來好好的企業搞死,造成幾敗俱傷、生産(chǎn)力遭到嚴重破壞的惡果。
改 革開放的過程,也就是還經濟發展權于民(mín)間的過程。而懲治民(mín)企原罪,恰恰是重新(xīn)剝奪和打擊了民(mín)間發展經濟的權利與權益,并且對國(guó)家民(mín)族中(zhōng)最有(yǒu)活力、最有(yǒu)成長(cháng) 性的經濟成分(fēn)構成打壓和威脅。這樣的不公(gōng)正命運既會落到已經有(yǒu)所氣候、有(yǒu)一定能(néng)量的民(mín)營企業家頭上,又(yòu)怎麽不會落到更弱的小(xiǎo)民(mín)頭上?觀察表明,由于仇富之 風和懲治民(mín)企原罪之風愈刮愈烈,在人人有(yǒu)罪的态勢下民(mín)營經濟界以彼觀已、設身處地,幾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并出現很(hěn)值得憂慮的動向。一是過去堅決守住“民(mín)族品牌”而不肯賣給跨國(guó)外資的優質(zhì)民(mín)企,現在急于求賣,德(dé)力西、華宇已經賣了,據了解正泰、統一潤滑油等很(hěn)快也要賣,使本來就所剩無多(duō)的民(mín)族品牌更加危急,這無疑是在激烈的國(guó)際化競争中(zhōng)損已而助外;二是衆多(duō)民(mín)企迫切尋求資金外流出境,什麽“原罪”、“現罪”,變現到國(guó)外都抹掉無罪;三是在懲治風下,民(mín)企老闆們大量地變生産(chǎn)資金為(wèi)消費資金,導緻企業資金環境更差;四是誰做大、誰就倒黴,誰就會成為(wèi)搶奪财富成果者們的衆矢之的。這充分(fēn)反映出改革開放20多(duō)年了,一些地方的一些人,還根本不能(néng)正确處理(lǐ)“财富問題”。“君子無罪,懷璧其罪”, 其結果是沒人肯去做大,沒人會認真發展企業、發展經濟。發展得越大,自己的罪責就越大,這算是什麽邏輯!?這對于中(zhōng)國(guó)的财富創造過程是緻命的。況且,追究 民(mín)企原罪往往并不能(néng)打擊腐敗,所打擊和毀掉的,恰恰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具(jù)生命力的、同時也深受權力腐敗之害的民(mín)營經濟,而腐敗勢力本身卻往往安(ān)然無恙,坐(zuò)收 漁利。懲治腐敗的善良願望反而助成了腐敗者的得勢,“追究者”們豈不慎乎?
三.經濟與法律權威人士提請特别關注的幾個問題
就塗景新(xīn)一案我與經濟界和法律界權威人士,如江平教授、賀衛方教授、錢衛清大律師等進行了交流探讨,發現在“懲治民(mín)企原罪會導緻中(zhōng)國(guó)經濟嚴重的發展危機,并對構建和諧社會造成嚴重損害”這一判斷上大家有(yǒu)高度共識,并共認有(yǒu)幾大司法不公(gōng)傾向和社會危險傾向須提請全社會給予特别關注。
(一)在處理(lǐ)民(mín)企經濟法律關系方面,往往民(mín)法、刑法兩者不分(fēn),而且動辄将本來屬于民(mín)事糾紛的問題随意上升為(wèi)刑事矛盾,高調介入,先抓再審,抱着“不信就找不到你的毛病”心态辦(bàn)案,先定有(yǒu)罪,後找罪證,長(cháng)押不審,長(cháng)審不決。這一方面是司法水準素養的問題,另一方面更根本的還是文(wén)革“以階級鬥争為(wèi)綱”思想的餘毒表現,動不動就上升到“敵我矛盾”性質(zhì),與我國(guó)司法原則上越來越重視保護公(gōng)民(mín)正當權益、越來越強調“民(mín)事為(wèi)本”的方向明顯背離。這決不是“和諧社會”應有(yǒu)的指導思想。衆專家一緻認為(wèi),司法實踐中(zhōng)對相應的問題應确立“先民(mín)事、後刑事”的原則。象塗景新(xīn)案,如果确立了産(chǎn)權的民(mín)營性質(zhì),就根本構不成任何所謂的“貪污犯罪”。轉型期中(zhōng)社會現象格外複雜,司法實踐中(zhōng)“民(mín)事關系”更為(wèi)根本,郎鹹平式的“嚴刑重典論”根本上是錯誤的,對構建“和諧社會”有(yǒu)非常大的背離性和破壞性。
(二)轉型期我國(guó)在司法制度及其他(tā)制度的供給方面有(yǒu)嚴重的缺陷,導緻民(mín)企行為(wèi)的種種扭曲,但在處理(lǐ)相關法律矛盾時往往不講曆史過程,不看時代背景,往往由民(mín)營企業家獨自承擔時代缺陷的各種過錯。時代發展的缺陷和多(duō)方因素懷導緻的過錯卻讓企業家單獨“買單”,等于是對20多(duō)年來改革中(zhōng)民(mín)營經濟的發展實行不合理(lǐ)清算,往往造成幾敗俱傷的惡劣後果,造成對生産(chǎn)力不應有(yǒu)的嚴重破壞——請那些以“公(gōng)正”之名(míng)追究民(mín)企原罪的人士想一想,這樣做究竟有(yǒu)什麽公(gōng)正?對經濟行為(wèi)的判定要考慮時代背景,這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連美國(guó)這樣的國(guó)家都是如此,都要充分(fēn)論證和區(qū)分(fēn)時代因素與個人因素,更何況象中(zhōng)國(guó)這樣處在跨度極大的體(tǐ)制變革過程中(zhōng)的“轉型社會”。我認為(wèi),在社會仇富心态急劇上升、懲治民(mín)企原罪的錯誤指導明顯擡頭的情況下,要特别警惕用(yòng)民(mín)企和民(mín)營經濟做社會替罪羊、做時代替罪羊的傾向,這不僅非常不公(gōng)平,而且最終受損的還是整個社會。
(三)根據曆史背景情況,有(yǒu)區(qū)分(fēn)地适當赦免民(mín)企原罪,仍是打破民(mín)企危機、進一步發展經濟、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課題。去年12月我本人向中(zhōng)國(guó)立法機構發出“解脫民(mín)企原罪”的公(gōng)開信,提出一定要将“原罪”與“犯罪”區(qū)分(fēn)開來,并區(qū)分(fēn)了三種“原罪”給予赦免解脫。一是“改革性的探索原罪”,同時也是改革界線(xiàn)不清産(chǎn)生的無知之罪;二是配合地方政府推進地方經濟發展而進行的“跟随違法”,是一種“發展性的被動原罪”;三是法不責衆的“行規慣性”延續,由此産(chǎn)生出“普遍性的道德(dé)原罪”。
此信一出,争議如潮,輿論嘩然。一些人認為(wèi)這是替“有(yǒu)罪的富人”開脫,有(yǒu)些人認為(wèi)是“助長(cháng)腐敗”。比較通情理(lǐ)的看法也認為(wèi),“原罪問題”綜 錯複雜,宜做不宜說。但問題恰恰在于,正如上面所舉案例(以及未舉的更多(duō)案例)所表明的那樣,你不說、不揭明真相,國(guó)家和人民(mín)就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被一 些别有(yǒu)用(yòng)心的人把我們的民(mín)營經濟發展大好局面一步步毀掉!在就塗景新(xīn)案與法學(xué)權威們的讨論中(zhōng)我發現,在必須就此揭明真相、澄清原則方面,專家們恰有(yǒu)超出我 預料的高度共識。如江平教授就認為(wèi),要特别注意“人為(wèi)的法律陷坑”現象。即是說,有(yǒu)些經濟交往中(zhōng)的違規違法行為(wèi),執法機關長(cháng)期不做糾正,變成了人人皆為(wèi)的“行業潛規則”後,卻突然要嚴格執法,過期追訴,很(hěn)容易變成陷人于罪的“法律陷坑”。這正是我所提出的“法不責衆下的行業慣性,形成普遍性道德(dé)原罪”的情形,即“第三種原罪”的情形。幾位專家都提出要特别警惕“全民(mín)皆罪”現象,即賀衛方教授所說的“總有(yǒu)一種法規讓你成為(wèi)罪犯”,讓你遭受刑事懲辦(bàn),由此構成了目前全社會對私有(yǒu)财産(chǎn)整體(tǐ)高漲的仇視心理(lǐ)的司法表現,“會成中(zhōng)國(guó)今後發展很(hěn)大瓶頸”。這與我提出的“打破民(mín)企原罪危機”的呼籲不謀而合,也是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多(duō)位專家都認為(wèi),中(zhōng)國(guó)民(mín)營經濟生長(cháng)于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不規範環境”中(zhōng),很(hěn)容易出現“罪”與“非罪”界限含混模糊的狀态,對這個仍不成熟的初生兒“不宜濫用(yòng)猛藥(尤其是郎鹹平式的猛藥)”,更不能(néng)搬用(yòng)“文(wén)革思維”。濫用(yòng)猛藥與文(wén)革思維隻能(néng)打掉民(mín)營經濟的改革成果,而這正是中(zhōng)國(guó)改革成功的核心特點所在。如果執意要民(mín)企去做整個社會曆史不規範的替罪羊,最終受損的還是社會,受損最重的可(kě)能(néng)還是弱勢群體(tǐ),使他(tā)們弱上加弱。從中(zhōng)亦可(kě)看出,“遠(yuǎn)離文(wén)革”仍是今天今天社會最根本的環節所在。